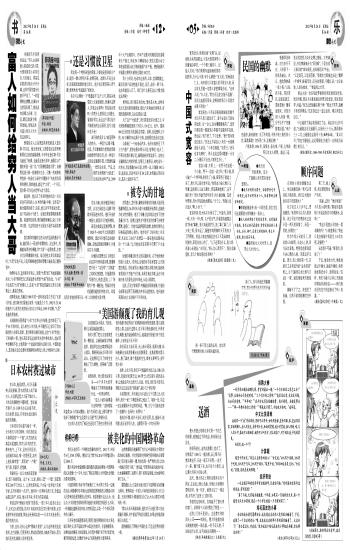总有人痛心疾首地批评商业文明,认为它导致世人沉醉于物质享受而迷失自我,他们开出的一剂药方,就是学习甘地好榜样。
著名的美国记者夏伊勒,曾于1925年-1932年之间报道印度新闻,因此与甘地有过亲密的接触。在他近距离的观察中,甘地存在不少局限。
甘地的治国理念在《印度自治》这本书里坦诚呈现,离谱程度不差于“乌托邦”、“太阳国”之类的幻想国度。甘地强烈排斥现代化,铁道、医院、工厂等现代产物一概拒绝;凭着具有绝对道德优越性的传统文化,印度人民在甘地的带领下以一穷二白的物质生活为荣。
在私德上,苦行僧、清教徒形象的甘地被人批评是愚蠢和荒淫。36岁时未与妻子商量就开始禁欲,这被视为对女性的蔑视。他为了非暴力信仰而认定皮下注射是暴力行为,拒绝让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的妻子注射青霉素,遂病亡。甘地为远离罪恶而食素,食物仍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精心制作;他穿的手工纺织的土布衣服,未必比工业化产品便宜……曾在他身边服务过的一个人说:“让甘地生活在贫困中花费了不少金钱。”
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之所以能胜利,在于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敌人。很幸运,甘地的对手是有宽容、公正制度的英国。评论家乔治·奥威尔曾以苏联为例,指出唯有英国治下才能产生甘地。如果甘地在苏联,会在半夜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带走,从此人间蒸发。
因此,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得很刻薄:甘地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英国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