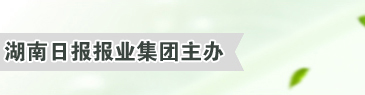夜已深了,医院走廊的灯依然亮着。超声科的房间里,一个光头俯在显示器前,眼睛几乎贴上了屏幕。窗外偶尔有救护车的鸣笛掠过,他却浑然不觉,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着,不时停下来翻检手边的资料。
24年前,命运将他推到超声科医生这个位置,他便认了。土家族的血脉里流淌着一种固执,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那些年,他像着了魔似的,白天看病人,晚上啃文献,将《The Fetus》(《胎儿医学》)上的病例一篇篇译成中文。灯光照在他日渐稀疏的头顶,同事们戏称他“光头强”。
“医生,我的孩子……没事吧?”一位孕妇紧张地攥着检查单,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嘴唇,仿佛那里即将吐出的是生死判决。他调整探头,凝视屏幕,那些色块在他眼中自动组合成清晰的解剖结构。多年的经验让他能一眼看出异常,但他仍仔细检查每一个切面,不放过任何细节。
“目前看是正常的,”他终于开口,“但胎盘位置偏低,需要定期复查。”孕妇长舒一口气,眼泪却下来了。他递过纸巾,心想,又一个生命在他的探头下被“看见”了。这大概就是他坚持的理由——那些被他“看见”的生命,那些因他的坚持而得以延续的希望。
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常备着止痛药。神经性头痛发作时,那种从耳后直窜头顶的剧痛,像有人用锥子凿他的脑壳。今年5月那次发作尤为厉害,他几乎是扶着墙走进诊室的。他只在值班室躺了半天,下午又出现在诊室。“病人等太久了,”他对劝他休息的护士说,“能看一个是一个。”
科室的墙上挂满了奖状,那是他和团队3年来的成绩。有人称他“拼命三郎”,他倒不觉得这是什么褒奖。只是每当看到候诊区那些焦急的面孔,他就无法心安理得地下班。那些抱着大肚子来回踱步的孕妇,那些拿着检查单坐立不安的老人,都在无声地催促着他。
晚上20时20分左右,最后一个病人离开。他瘫坐在椅子上,手指因长时间握持探头而僵硬。走廊的灯光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他忽然想起20年前那个在小隔间里挑灯夜战的年轻人,那时的他大概想不到,这份工作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他的人生。
超声科医生的世界是由光影构成的。黑白的图像里,藏着生命的奥秘;漫长的等待中,蕴含着希望的微光。而他,甘愿做那个执着的读影人,在光与影的交界处,守护着生命最初的形态。
汪越澄(湖南 湘西)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