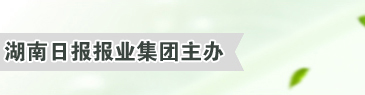清晨六点半,天还未大亮,初夏的风带着微凉的湿意。我站在科室的窗前,看着这座渐渐苏醒的城市。这样的时刻,我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
有人说,勤奋是一种习惯,可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种责任。
2006年3月,我来到这家医院。从那时起,七点半前到科室就成了铁律,后来渐渐提前到七点。八点前看完所有检验报告,标记异常,安排处理。手术室的灯常常因我而早早亮起,节假日的病房里也总有我的脚步声。这些年,我的足迹踏遍了郴州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永州的部分山区。可另一条路,我却走得极少——那是回家的路。
起初的几年,我总想着父母身体尚好,回去的机会还多。如今算来,二十年里,回老家的次数,仅是只有三次。
爷爷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电话里,父亲的声音沙哑:“你忙的话,不用赶回来了。”我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看着窗外的枯枝在寒风里颤抖,最终没能回去送他最后一程。那天的手术,我做得格外专注,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心里的愧疚稍稍平息。可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爷爷用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教我认字的情形。
2022年冬天,我把母亲接来住了几个月。可不到半年,她就执意要回去。“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总说,“你在医院忙,我在这反而让你分心。”送她上火车的那天,她蹒跚的背影在月台上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人群里。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小时候每次离家,她都会站在村口的那棵老树下,一直望到看不见我的身影为止。
有一年除夕,科室里格外安静。护士问我:“赵主任,您不回家过年吗?”我笑了笑,低头继续翻看病历:“这里也需要人守着。”她点点头走了,而我手中的笔却微微一顿——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母亲在电话里小心翼翼的声音:“你要是忙,就不用回来了,工作要紧。”
他们从不抱怨,可我知道,在每个团圆的日子里,那间老屋一定格外空荡。
医生这个职业,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病人来了又走,可责任永远在那里。我治愈了许多人,却唯独亏欠了最该陪伴的人。有时深夜下班,我会站在医院门口,望着北方——那是老家的方向。夜风微凉,路灯昏黄,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父亲在一旁翻看我的作业。那时的日子很慢,慢到让我以为,这样的时光永远不会结束。
如今,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里越来越轻,而我的白大褂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晨光里。新的一天开始,还有病人在等着我。而远方的老屋里,母亲大概正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方向,想着她的儿子今天有没有按时吃饭。
这世上有一种遗憾,叫“等以后”。可岁月从不等谁,有些告别,一旦错过,就是永远。
赵玉国(河北)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