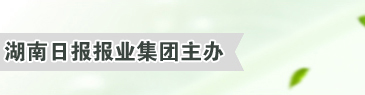2023年,我17岁,生命像一张拉满的弓,弦上搭着的,是一支名为“高考”的箭。
变故,是在一个寻常的薄暮时分来的。尖锐的刹车声,玻璃碎裂的嘶鸣,然后是巨大的黑暗。再醒来时,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病房墙壁那种刺目的、了无生气的白。痛楚是后来才慢慢苏醒的,像无数细小的、烧红了的针,从四肢百骸深处扎出来。
病例上赫然写着:腰椎、肘关节、双侧桡骨、股骨、腓骨……每一个后面都附着“骨折”两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字。医生语气出奇的平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走路。”
很长是多长?会错过高考吗?这些问题在我喉咙里打转,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万念俱灰。
康复治疗从最简单的动作开始。“今天的目标是抬起手臂,五厘米。”吴医生的声音温和而坚定。我咬紧牙关,调动全身的力气,汗水顺着鬓角流下,可那只属于我却又不听使唤的手臂纹丝不动。
日复一日,病房成了我全部的世界。最初的狂躁与绝望过去后,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更深的、黏稠的倦怠。
那一天,吴医生推着我的轮椅来到了康复大厅的窗边。“看见那棵树了吗?”他指着窗外一棵枝干扭曲的老树,“它去年被雷劈中,都以为活不成了。现在,你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在那焦黑的裂痕旁,嫩绿的新芽正倔强地探出头来。
“子杰呀,生命有自己的智慧,它知道如何在不完美中找到新的出路。”吴医生如是说。
那天之后,我不再把康复视为惩罚,而是当作一场新的学习。学习如何与这具受伤的身体和解,努力推开走向健康的那一扇门。
我开始注意到其他病友——因中风而重新学走路的老爷爷,失去一条腿却依然笑呵呵的快递小哥,因意外烧伤却坚持来做复健的女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我们成了彼此无声的见证者。
大半年后,我第一次靠着助行器站了起来。双腿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全身的重量压在腋下的支架上,疼痛如电流般窜过脊背。但当我从站立的高度重新看这个世界时,泪水模糊了视线。
医生说我的康复是个奇迹。但我知道,奇迹的另一个名字叫“坚持”。就像种子在岩石的裂缝中发芽,只要有那一道透进来的阳光,就会有生的希望。
窗外,那棵老树的伤痕被新绿温柔地覆盖。而我也迎来新生,我将坚定地走向那不一定完美却足够宽广的未来。
张子杰(湖南 张家界)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