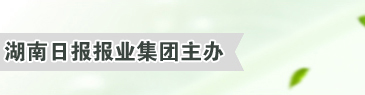北方的风总是硬的,像奶奶皲裂的手指关节。奶奶站在菜地边上,灰白的头发被风吹得蓬乱,像一丛枯干的蒿草。
今年春天的消息是裹在谎言里来的。爸爸说奶奶只是肠子里长了点小疙瘩,切了就好。我隔着电话听着,心里的石头轻轻落了地。直到某个深夜,爸爸的醉话像冰锥扎进来——癌细胞早就在扩散了,手术只是撕开一道口子,后面的路要靠化疗硬闯。挂了电话,窗外的月光突然变得很冷,我抱着膝盖坐了整夜,手机屏幕亮到天明,搜索框里全是“直肠癌、化疗”的字眼。
五一恰逢奶奶的生日,我决定回家探望。
推开家门时,我看着她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背影比记忆里缩了半截,像一株经了霜的芦苇。
“回来啦?灶上炖着你爱吃的排骨。”她的关心笨拙得像学步的孩子,却一下下踩在我心上最软的地方。
关于化疗的讨论是在院子里进行的。爸爸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圈在风里散得很快。“副作用肯定大,但不做……”我打断他,声音发紧,“她那么怕疼,知道自己得的是这病,说不定扛不住。”后来才知道,她每次化疗回来都吐得昏天黑地,却总在我们面前挺直腰板。
离家那天,我在巷口等车,听见菜地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奶奶踩着露水跑过来,裤脚沾着泥土,手里攥着个布袋。“路上饿,煮了鸡蛋。”布袋沉甸甸的,我笑着推回去:“太多了,吃不完。”她却直接塞进我包里,指腹蹭过我的手背,带着泥土的凉:“拿着,顶饱。”
列车启动时,窗外的白杨树向后退去。我把布袋放在膝头,手指摸到袋底的硬纸,抽出来一看,4张百元纸币叠得整整齐齐。前几天她问我路费多少,我随口说四百多,小老太太当时没说话,只是往灶膛里添了块柴。
眼泪突然就决了堤。这个一辈子在针尖上省日子的人,总把最宽绰的爱留给我。
鸡蛋的温热渐渐散去,但那份温暖却永远留在了我的掌心。这份爱,足以支撑我走过人生所有的寒冬,也让我虔诚地祈祷:愿时光能对她温柔些,让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能多看看这个世界的晨昏。
李开欣(山西 运城)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