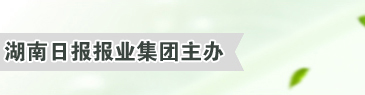我和这世间所有人一样对母爱上瘾,而我的瘾在2017年8月的一个下午,被生生割离——母亲走了。
这种瘾时常发作,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往复折腾,梦境尚还好说,但现实的触景伤情却一次又一次诱发我的泪点。
傍晚独自去机场散步,一辆小黄车满满敦敦地载着两个大人从我眼前晃过,暗想这人也真是,那么个小电驴还要带人,不把轮胎给压扁了。仔细看时,却是五十几岁的女儿带着七十多岁的母亲,母亲搂着女儿的腰,一脸笑意安详。女儿紧紧握着龙头,不时快速扭头看一下身后的母亲。我被这一幕暖到了,眼内不由自主起了雾,对号入座地想起了母亲。
那年带着母亲去土地主农庄玩,她那股高兴劲差点从身体里飞出来,眉梢眼角全是笑意,她一遍又一遍地和我说,妹妹,我很喜欢这里,真想到这里租间房,在这里种菜养花喂鸡喂鸭,我做最好的饭菜给你吃。如今每次重游,都不自禁地低头吮吸,农庄的一草一木间皆有母亲温和柔软的气息。
我知道母亲对我也有瘾,有我的地方,她就格外知足与幸福。闲下来时,我又会认真评估母亲的瘾,倘若她能坚固些、抗压些、钝感些、争气些,扎扎实实地活着,我们彼此的瘾不就能得到很好的平衡与满足了吗?实在太想太想她,有时候家里哪怕是进了一只飞蚊或是一只蚂蚁,我都怀疑是母亲所变。
出于羡慕与嫉妒,我不想听朋友们谈论自己的母亲。“我妈今天炒了鸭,一定要我去吃,其实我这几天吃鸭都吃腻了。”听到这话就要沉不住气地抵触,有妈的日子像块宝,麻烦你珍惜点。“我妈今天过生日,我得赶紧回家做饭去。”我喜欢听这话,可这样的话多刺激人,明明知道我没有母亲,还要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朋友们都聪明,她们活得比我明白通透,四十几岁时父母健在的是福气,父母没在的也很正常。更有甚者,竟说,你算好了,谁谁谁的母亲在她几岁上就过世了。
我也越来越明白通透,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深受。
她们的母亲还活着。
很感激黄姨,有段时间我几乎把她当成了母亲,也让我着实过了把瘾。黄姨的女儿是教我太极拳的师父,和我年纪相仿。有阵子我师父特别爱吃北街一家店里的小发糕,我们练拳的地方距那家店步行往返差不多要半小时,黄姨一早就跑去那家店买发糕。每回将热呼呼的小发糕递给女儿时,黄姨那一脸宠溺的表情让我看傻了,也看伤了心。我背过身佯装继续练拳,眼泪却不由自主地落下来。“田妹崽,等下再练,先吃发糕,姨也帮你买得有呢。”黄姨拉起我的手,将几坨热乎乎的发糕塞到我手里。我的泪水流得更欢了,黄姨拿起纸巾轻轻帮我擦掉眼泪,“不嫌弃,就把我当成你的妈妈吧。”
后来,我去黄姨家蹭饺子蹭饭,也算过了把女儿瘾。我至多吃八个饺子就饱了,虽没有师父对饺子那么深厚的美食感和获得感,但也觉得那饺子的确实比外面卖的好吃多了。硬生生又牵扯出小时候的回忆。那时父母亲经常在家里和老面做包子,做的包子可不比外头的差,不仅个大蓬松,里边包的肉馅也是大坨大坨的,大哥每餐要吃五个大包子,小哥吃四个,就我老嫌家里做的包子不好吃,母亲给我打包两个到路上吃,我咬两口就扔掉了,再拿了钱偷偷到外头买别的吃。倘父母亲知道我曾经把他们引以为傲的给孩子们做的最好的早餐那般糟蹋,还不知道该怎样数落我,或者干脆打一顿。现在我超级后悔,特别想念他们做的那些包子馒头,他们要是活着该多好啊!
师父的女儿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后,黄姨只身前往北京陪读,七十几岁的年纪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儿孙们付出。母亲在世也是这般为儿孙操持。那段时间,我特别想念在北京的黄姨,想她做的吃食,想她温和柔软的话语。我居然和所有的学生一样巴望着放暑假,放假黄姨就回来了,她一回来准会喊我去家里吃饭。吃完饭,黄姨还有礼物送我,一瓶来自上海的老牌雪花膏,精致的圆形小铁盒上一个美女甜甜地笑着。抚摸着这盒雪花膏,我半天才说:“黄姨,你对我真好。”黄姨朝我慈祥地笑着,那一刻,我真想喊一声妈妈。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看黄姨了,等事情缓些,也该去看看她老人家了。
芷江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田玲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