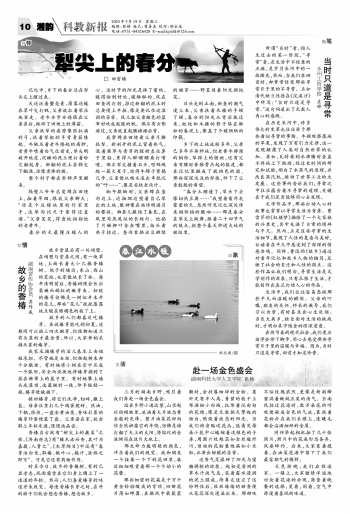□ 田雪梅
记忆中,乡下的春分总在犁头尖上醒过来。
天还泛着蟹壳青,薄雾还蜷在草叶尖打盹,父亲就扛着犁往地里走。老牛亦步亦趋跟在父亲身后,踩碎了田埂上的薄霜。
父亲扶犁的姿势像张拉满的弓,扶着犁耙的手背青筋隆起。牛轭压着老牛隆起的肩胛,老黄牛喷着白气往前走,犁尖刚破开地皮,沉睡的泥土便打着哈欠翻起身。新翻的泥土在铧尖下翻涌,活像煮沸的粥。
整个村子都在犁铧声里醒来。
隔壁三爷爷总爱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跟我父亲聊天:“你是个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这犁沟比尺子量得还直溜。”父亲笑笑,得意地指指他的老黄牛。
春分的天最懂庄稼人的心。这时节的阳光是掺了蜜的,暖得恰到好处,暖酥酥的,风在田垄间打转,掠过新翻的泥土时总要慢上半拍,像是要记住这湿润的芬芳。风儿把父亲褪色的蓝布衫吹成鼓胀的帆。偶尔有云影游过,父亲就直起腰捶捶后背。
我常蹲在田埂看父亲弓腰扶犁。新剖开的泥土冒着热气,混着腐草与青芽的腥甜直往鼻子里钻,熏得人醉醺醺要打喷嚏。偶尔犁尖撞着石头,哐啷溅起一簇火星子,惊得牛蹄子紧捣几步,父亲便从喉头滚出串低沉的“吁——”,像是安抚老伙计。
晌午歇晌时,父亲蹲在垄沟边上,边抽烟边望着自己犁出的土地,眼神像在端详刚满月的婴孩。柳条儿蘸饱了春色,在风里写燕尾似的长短句。他掐了片嫩柳叶含在嘴里,抬头看燕子掠过。垄沟里拱出豆瓣绿的嫩芽——野菜顶着阳光朝他笑。
日头走到正南,新垄的潮气漫上来,父亲扶着木耧的手顿了顿,春分的阳光从背后拢过来,把他和木耧的影子烙在酥松的春泥上,像盖了个暖烘烘的印戳。
乡下的土地流转多年,父亲已多年不再种地,但老黄牛脖颈的铜铃、犁铧上的锈斑,还有父亲弯腰时脊椎骨凸起的弧度,都在记忆里酿成了琥珀色的酒。那些深深浅浅的犁痕,种下了父亲殷殷的希望。
“春分土醒透了,犁头下去像切热豆腐……”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忽然听见记忆深处传来铜铃铛的脆响——那是春分在犁尖上跳舞,踩着二十四节气的鼓点,把整个春天种进大地的皱纹里。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502000374号